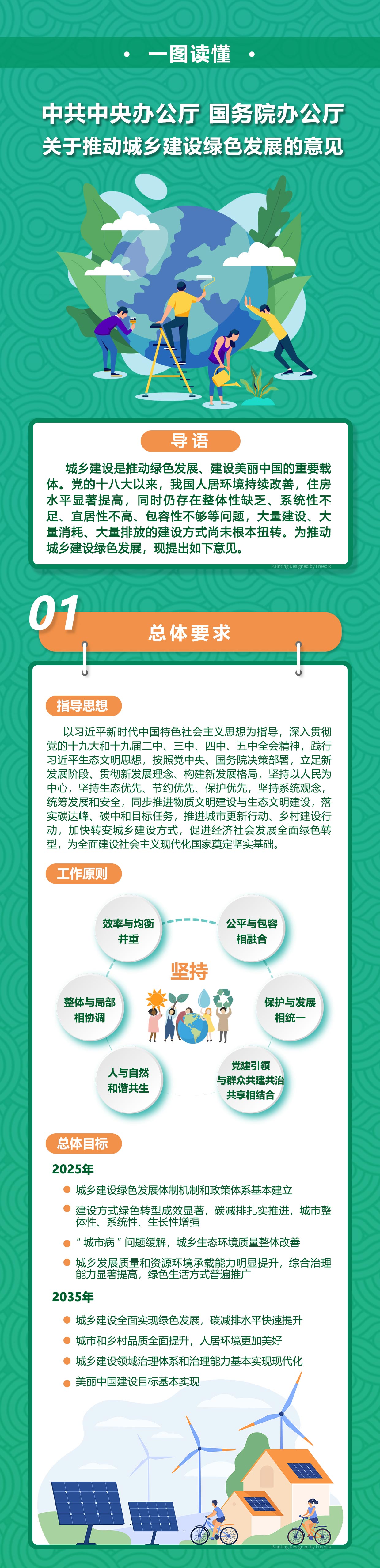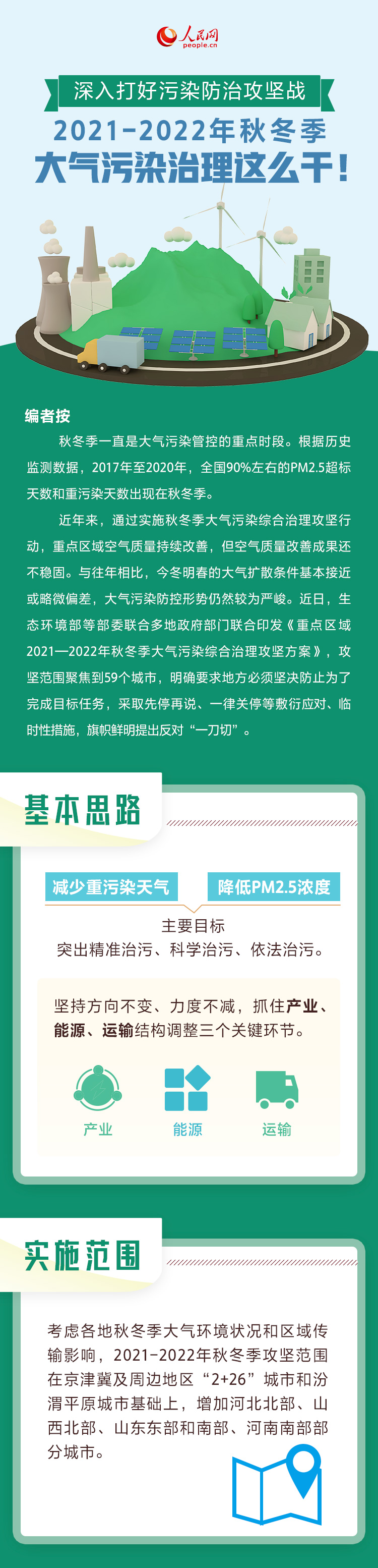高适与李白,到底殊途同归
《长安三万里》的结尾,如同一场大型飞花令。不同音色声线、不同口音的人们读出一句句诗词,其中的关键词,就是“长安”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长安,文人心里的白月光
这些诗句,仿佛印证着片中高适历尽千帆后那句“诗在,书在,长安就在”的喟叹。写念念不忘,写欲罢不能,写月色,写春色,写秋日的落叶,也写离别的回望……有唐一代,诗人们的锦心绣口,付与长安多少偏爱,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足以在浩如烟海的词句中分拣归拢,咀嚼琢磨,再搭建起盛世的依稀模样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也的确让人们看到了那“绣成堆”的盛景。那是年少的高适第一次来到长安时见到的景象。他怀揣一腔抱负,欣喜于入目的一片繁华。人与城,都是那样的光鲜亮丽,意气风发。但这花团锦簇的长安,亦是居大不易的长安,高适铩羽而归,在往后余生中,一次次尝试蜿蜒曲折的、通往长安的道路上。
同样执著于长安的,还有李白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中的李白,不只有放浪形骸、仙风道骨,更充满对功名的渴求、对做官的热切。那个坚信“少年负壮气,奋烈自有时”的李白被放大了,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豪气清晰了。兜兜转转,在李白心头,离长安更近的渴望、入仕一展宏图的夙愿始终不曾磨灭。
长安,不只是一座城;与长安有关的一切,也不仅指向盛世的万千气象。长安,是文人心里的白月光、朱砂痣,是理想的载体,是追求的志业,是岿然不动的精神标的。《长安三万里》,讲的正是这追寻的旅程。轮番登场的文人墨客皆前赴后继、从未停息,而他们的魂牵梦萦的长安,却总是缥缈遥远,求而不得。
“但是诗人多薄命”
求而不得,仍要孜孜以求。“你是谪仙人,要回天上,我是世间人,我在世间盘桓。”如片中高适所言,他与李白,便以迥然的姿态,纵身跃入人海,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难以抵达终点的路途。
在高适的回忆里,李白是何其独特而不凡的存在: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潇洒不羁的人,可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。”青年初遇时,高适文采平平、耿直木讷,李白惊才绝艳、放浪形骸。当李白流连于胡姬酒肆、扬州风月时,高适的生活里,是不断的磨练与蛰伏。终其一生,他们的性格与际遇都大相径庭;直至暮年,高适成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,李白成了潦倒落魄的阶下囚。
但他们真的截然不同吗?
治国平天下,是儒家最高政治伦理信念;做贤臣、辅君王、开治世,是古代文人的传统理想;求功名,入仕途,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被视为人生的意义与正途所在。“万里不惜死,一朝得成功。画图麒麟阁,入朝明光宫。”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曾被高适直截了当地剖白于诗中。直至晚年,在蜀州刺史任上的他还因“身在远藩无所预”而“心怀百忧复千虑”。高适如此,李白亦如此。影片中,李白一早便吐露了内心——总有一日,他要功成名就、身退得道。然而,这个被认可、被赏识、被重用的机会,他一直在苦苦等待。
高适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郁郁不得志是生活的常态。尽管他也在对官场黑暗不满的时刻自我宽慰,“我本渔樵孟诸野,一生自是悠悠者”,但仍在年近50岁时选择暂时放下高家枪,到哥舒翰手下做起曾不愿做的掌书记。
两个李白,都是李白
可以说,在现实面前,高适是清醒的,可李白不是吗?他同样清醒,但他拒绝接纳。他渴求功业,却一次次碰壁,到了长安,又被赐金放还。他其实深谙世间的规则,所以写得出干谒诗文,做得了上门女婿,能给永王连写十一首颂歌,关进监狱后给高适的求情诗也句句溢美之词。他懂得世界的荒谬、人生的悲苦,但他终究给自己与这世界画出了一道界线——他拒绝被同化,于是注定无法进入这尘世。
可他也无法彻底放下入世的理想,所以他同样做不到彻底忘名利、离竞逐、息攀比的出世,看不穿也悟不透,于是修道必然难有所成。他希冀以一己之力打破世间藩篱,一次次用洒脱不羁自我慰藉,不断在入世与出世间挣扎拉扯,所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,和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”的李白,都是李白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,李白与友人吟诵的《将进酒》的段落,是整部影片的华彩乐章。主创们历时一年半创作的这场戏,极尽恢弘壮阔、浪漫飞扬。随着吟诵的诗句,李白和友人击波涛,登天宫,与仙人把酒言欢,在琼楼玉宇穿行,鲲鹏白鹤,云霞星河,上天入地,瑰丽绚烂。而极致的浪漫、潇洒、豪迈,包裹的却是李白的悲凉、愁苦、愤懑。这首以“悲”而起的诗,收束在以酒消愁的豪兴,但酒意醒来,幻想散去,只余滔滔江水拍岸,一轮寒月高悬,和一个有了啤酒肚不复当年飒爽英姿的中年人。但愿长醉不愿醒,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,在一次次失意落寞中,李白仍不断渴望着理想实现的明天。
留下况味,令人欣慰
《旧唐书》评价高适:“有唐以来,诗人之达者,唯适而已。”或许,官至三镇节度使、封渤海县侯的高适称得上大器晚成,实现了“取得功名”意义上的成功,完成了人生理想。但这样的成功,又何尝不是政局风云变幻的产物、不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生?
李白的壮志难酬,以及杜甫、王维、王昌龄等一众文人的艰难困窘,亦是如此。就如片中那个女扮男装的裴十二,虽尽得裴家剑法真传,却因身为女子而无处施展——高、李与她的命运,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以诗人们具体的命运,铺展开一幅时代变迁的画卷。看过影片,会明白为什么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”,更会感慨为什么“但是诗人多薄命,就中沦落不过君”。
泸水关的中军帐里,年迈的高适再度回想起与李白初见时的模样。广袤旷野中,他们一言“在下李白”,一言“在下高适”,两个少年郎,皆风华正茂,渴望建功立业,这是他们共同的起点。他们的一生,尽管方式有别,境遇殊异,却都始终不曾离开由此延展出的人生路径。片尾,高适卸下铠甲,再度策马驰骋而去——那一刻,他与李白,到底殊途同归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就是追逐理想的三万里。回望那段人类群星闪耀时,一众文人墨客登场、退场,不断奔向那从未寂灭的理想之地,信念不绝,理想不灭,盼望着“心中的一团锦绣,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”。当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影片将这份豁达和虚无的况味留下。
一同留下的,还有思考的空间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如何选择和定义自己的人生?要介入现实还是抱持理想?求而不得是否还值得追求?凡此种种,影片没有评判,没有说教,始终清醒平静,温和包容。作为一部在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片,《长安三万里》注定要面对许多年幼的观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抛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、克制住自我表达的旺盛输出,远比华丽的视觉效果、动人的故事情节,更加令人欣慰。
标签: